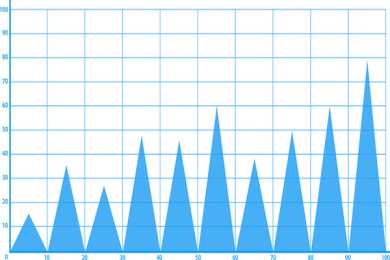参军那年,正赶上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全公社沉浸在一片低沉和悲伤中。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能够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我们乡邻中炸开了锅,这是一件光耀门楣的大喜事,许多长辈见到我都笑着点下头。
我们村加上我一共去了三个兵。送兵那天,全公社去参军的新兵们统一乘坐公社配发的解放牌卡车。
我扛着被褥,刚挤到我们村几个老乡身边,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喊我的名字,扭头看到邻村一个高中毕业的扎着长辫的女孩。
她叫余跃文,读高中的时候,我俩是一个学习小组。那个时候高中升学率很低,我们高中一毕业便不约而同的回乡务农。
临上车时,看到她胸前戴着的大红花,我知道她也是入伍参军的新兵,就这样我们一起开启军旅之路。
汽车开动了,卡车后厢板放下,新兵和前来送行的乡亲们用力挥着手,女人们的哭声在空气中回荡着,一声声叮嘱的话飘散在风中。
到了县城,男女新兵分开体检,再次见到她是在新兵集中准备出发的招待所了。我跟余跃文分到了不同的部队。
临别那天,她眼含热泪,对我说“苟长远,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看我。”
火车载着我们这些新兵开往中原大地,两天后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车站。
车站很小,从上下来的军人很多。车站的一侧整齐地排列着近百辆解放牌军车。各部队来接兵的干部早就在等候着,拿着花名册仔细地核对完新兵人数,一声“出发!”军车载着我们奔向各自的营房。
一路尘土飞扬,天黑时分,汽车稳稳停在营房外,我才注意到这是一座建在丘陵地带、四周都生长着一人高的杂草和灌木的营房。
进了营房,我们几个人按照高矮顺序排列,来接兵的班长把我和另一名叫黄德安的新兵,分到一起。
“从今天开始,你们二人要团结,生活上互相照顾,思想上互相帮助……”“是!班长。”我和黄德安异口同声大声应着班长的话。
营房里十分简陋,一个连队百十号人,没有独立的床铺,都是顺着墙边两溜长长的大通铺,中间留有一个过道。
铺上整齐地摆放着军被,床头的墙壁上贴着毛主席的头像,还有用各色彩纸剪出的标语: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等。
我们是装甲兵,在那个年代,全国的装甲兵屈指可数。军人地位很高,能开坦克那绝对是很令人自豪的事情。
刚到连队那些日子里,我的耳边总能听到轰隆隆的发动机声,老兵开着笨重庞大的坦克训练归来,一群老兵围坐在水龙头下用自制的长长的橡皮管洗澡、戏耍,总能引起我们的好奇。
坦克的轰鸣声让我热血沸腾,可命运没有安排我去开坦克。在新兵连三个月,我和黄德安被一同分到了坦克修理厂做了一名学徒工。
那时,修理厂坐落在一个小山坡的底部,几排红砖红瓦房被参天的大树遮盖,十分隐蔽。一进厂门,路两旁摆放的报废坦克和拆解下来的零件,提醒着每一个进入修理厂的人,这里的任务是多么的特殊。
修理厂没有围墙,山脚下有连队执勤站岗。进入厂区上班要登记。
与我同批分来的五个战友都是学徒工。
一个安徽籍的老班长告诉我们:我们五个分别要跟不同的师傅学习机械维修。机械修理有车工、钳工、焊工和电工。
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个人命运的安排通常没有太多的选择,部队需要你做一名车工,你只有服从命令。
我们部队没有二炮手这个称谓。坦克里分别有车长、炮长、驾驶员和一个装填手。
班长在介绍完修理厂情况后,问:“苟长远,你的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应该在初中学习过几何吧,懂机械制图的基础原理吧?就去学车工吧。”于是,我被指定学车工,成了李富贵师傅的徒弟。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跟在李师傅屁股后面打杂,师傅检修机床或者坦克的时候,我在一旁递送工具和零部件,眼睛仔细看师傅维修机床和各种部件的全过程。
师傅维修完毕,要进行实测和演练,我拿着小本子进行详细地记录。我从不主动说话和插话。
师傅很满意,说我是那块料。
车工的技术性非常强,厂里的四级工屈指可数。我的师傅李富贵,河南安阳人,他在全师组织的专业技术比武中连续拿了两次第一名,破格由战士直接提干,被师里表彰为“技术能手”。
能够给这样的“兵头将尾”做徒弟,自然让很多人眼热。后来得知,我们同一年来的其他新兵基本没有转成士官都退伍了,当然这里还有一段后话。
白天上班时间紧凑而充实,我总抓紧时间去观察,去记忆各种操作的要领,晚上,自己一个人坐在小本子上反复勾画各种机械原理图。
我们师坦克修理厂,承担着全师的坦克维修保障任务。我平时接触较多的是车床和常用工具,而工具就是师傅手中的长短不同的小榔头和扳子等,每每看到师傅手里这些工具如玩杂耍般的娴熟使用,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
车工最常用的卡尺,师傅闭着眼睛一卡,报出来的尺寸,精准到我必须认真查看标尺才相信,有时候我甚至暗自怀疑师傅真的具有火眼金睛的能力。
师傅常对我讲:“我们手里的工具,就如同战士手里的枪,要每天认真擦拭保养。”
跟在师傅身后学习一段时间后,师傅便开始放手让我自己操作,出现错误或是我完成不了的任务,他及时帮扶指导。
三年后,我就已经能够独自修理常见的坦克部件了,而且多次受到车间和厂里的口头表扬。部队三年义务兵期满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退伍,连队的班长、排长、连长还有指导员,不断地做这些想复员回家军人的思想工作,而选择在部队转为志愿兵或者继续留队的人,多数都有现实的原因。
部队军人的婚姻是一道必须迈过而且难度比较大的坎儿。
老班长在给连里人上完课后,专门给我们几个参加过师里组织的学雷锋先进集体巡回报告会的人谈心。
他把在全师引起强烈反响的余跃文,安排在了第一个。那时候,全国已经开始有了高考制度,各个大学陆续复课复学,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国家对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常渴求。
记得那年七一建党节期间,我代表师坦克修理厂给各兄弟部队介绍了“从技术白丁成为修理业务骨干的经验做法”的报告后,便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继续留队转为志愿兵的申请报告了。
可没有想到指导员主动找到我,鼓励我积极追求上进,让我抓紧写转志愿兵的申请书,理由是我连续两年获得团里嘉奖、两次被师修理厂树为典型,转志愿兵不会有啥困难,我高兴的立刻应允。
那一年的深秋,我接到了在师部机关幼儿园担任保育员工作的余跃文来信,字里行间,看的出来她还是在想我。
我利用周六的时间,按照地址找到她后,一起看了电影吃了顿西餐。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马路漫无目的地的闲逛,谈了很多工作、训练、学习的经历。
我隐约感到,我对部队的那份执着,似乎更坚定了。
又一个秋风瑟瑟落叶飘零的季节走进了我当兵的生活,在转志愿兵的手续正在层层报批的时间里,部队进行调整,按照上级安排部署,我要离开工作7年的部队,内心真是五味杂陈难以接受,可必须无条件执行和服从部队的命令。
那段时间,我们几个人被连长单独留在办公室,连长耐心地告诉我们“无论地方上有什么政策优待,从地方那里来的到地方上去”的决定是铁的纪律,谁也没有能力能更改。
离开部队那天,厂里的战友们在暮色苍茫中为我们举行欢送仪式,师政治部的军务科的一位科长告诉我,经部队与地方协商后,我们几个都将回到原籍所在的县进行工作安置。
科长鼓励我们这些当了几年修理工的军人们,“不要灰心,你们是四级工了,组织上给的51元的工资定级是完全考虑你们实际情况的,要知道在地方这工资标准不低。”
抱着沉甸甸的理想,装着一颗火热奉献过的赤诚,我和同乡战友们就这样坐着火车回来了。
回到地方上,我被安置到了县农机公司,一个月工资是五十多块钱,那个时候这算是县里的高工资了。
我和乡里的其他退伍回乡的军人们常常谈到曾经为之奉献过的部队时,心里总是热热的,因为青春永远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燃烧、熔炼过。
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化,即使是部队安排的工作也可能面临变动,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并且适应环境,做出理性的决定,并且乐观积极地努力,或许人生就是一段体验!
(本文为小说故事,存在艺术情节,请理性阅读)